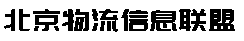铁可折,玉可碎,海可枯,不论穷达生死,直节贯殊途。(南宋·汪莘《水调歌头》)
人的骨气,是灵魂的骨头。一个人必先有灵魂,然后才可能有骨气。骨气是骨子里的东西,它首先是一种气质、一种人格,然后是一种人格深处的高贵。
中国第一个有骨气的文人,无疑是庄周。他的出现让中国人开始走向内心深处。时空中从此有了另一类人的灵魂出没,让我们有可能在心灵的高度发现人和世界的另一种存在方式。他以一生在潦倒中的坚守,最终把自己变成了中国文人的一个精神源头,也为更多的人摆脱生命的庸俗找到了一条可能的途径。
尘世是把双刃剑,可以磨蚀掉人格,也可铸造出人格。入世的文人,也不乏有骨气者,如屈原的正道直行。如果没有庄子,我们从一开始可能就少了一种自由的精神;如果没有屈原,我们从一开始可能就少了一种伟岸的人格。因为庄子,我们有了一个世界之外的世界;因为屈原,我们在世界之内有了一个坚实的底部。从屈原开始,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崇尚伟大心灵的时代。
在庄子与屈原之后,中国数千年文人的历史,实际上是这两种人格交替讲述的故事,无论是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方孝孺还是其他有骨气的文人。尤其是被灭十族的方孝孺。中国从来就不缺乏有才智、投机钻营的聪明文人,却太少了方孝孺这样有气节的文人。在方孝孺之后,中国文人中更加巩固了那种恪守和捍卫正统性和既定秩序的气节。
一个人的人格,是因为先有了灵魂,然后才有骨头。而要把一种人格一直保持下来,保持一生,几乎都是一种长期的受难。那些把自己的人格一直保持到最后的文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命运最悲惨的人,他们的灵魂无一不在精神与肉体的炼狱中把血熬干,最终只剩下了灵魂和骨头。而他们灵魂的骨头,最终构成了中国古典人文精神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