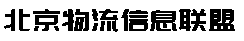近期有研究指出,某些人体生物标志物的发现,与AD及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生理病理相关联。这对既往临床谱概念、疾患检测与医学解读产生了巨大影响。AD作为最常见的痴呆类型之一,已有研究证据提示,AD患者在发病症状及 体征呈显性之前,其在人体身上的病理生理过程早已存在。为此,美国国立衰老研究院与阿尔茨海默病协会(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 and Alzheimer's Association,NIA-AA)对此类证据进行系统分析并指出,“AD是一个发展性的病理生理综合征,强调AD临床试验前期的内涵;不建议把相关研究用的标准用于临床诊断”。特别是针对符合此类研究标准的受试者,其状况进展在随后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患者终生,并不出现AD临床指征。另外,也有欧洲研究协作组阐述无症状AD风险分期,指出相关病理生理标志物在此阶段所扮演的角色,及当前 基于研究初衷所作的疾患类别。然而,基于脑组织、血液、基因及脑脊液等生物学标志物的研究,让AD疾患外延涉及的伦理学问题日趋复杂化。
其一,试验主体从既往有显性AD症状的患者,到当前基于病理标志物的无AD症状受试者,这两者之间的转变将产生怎样的伦理层面的效应?
其二,存在AD风险的高危人群,多数伴有不可逆转的认知能力下降,对此类受试者如何避免受辱、歧视等伦理问题?
其三,倘若当前对AD疾患尚无有效的治疗措施,基于此获取受试者疾患易感隐私数据,如何评估其临床价值及社会效益?
1.1 AD预防性试验风险/受益比问题
研究者对AD防治进行了一系列临床试验,即对相关疾患变化发展过程,在潜性易感基因或基于脑征象层面进行调控,旨在预防或延缓患者认知功能下降。既往针对有AD症状患者的临床试验干预(如β-淀粉样蛋白靶向化合物)未能有效改善患者认知功能下降的进程,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上述预防类研究的开展。为此,针对部分不存在显性记忆丧失症状、可经病理标志物标识高危状态的受试者,进行相关试验研究显得尤为重要。相对后期已有大量神经元缺失的病态阶段,在神经退行性变之前预先干预,显得更为有效。然而,在预防性试验研究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以下伦理学问题。
其一,受试者在试验初始阶段会被告知其处于AD风险状态,以获悉自身符合纳入标准的原因以及从该试验可能获得的受益。该过程应采取确切的安全措施,让受试者易感隐私及信息披露所致的伤害降低至最低。
其二,此类预防性试验纳入的部分受试者,或许因处于病理标志物阳性指征状态而符合研究入组标准,可在很长一段时间、或终其一生并不会转变为该试验干预所力求避免的病况阶段,即AD临床症状显性阶段。基于此,对上述受试者的试验干预,需采取合理的方式对其风险/受益比进行测评。
其三,纳入预防性试验研究的受试者,应综合考虑其对参与试验的风险及可能获取的潜在受益是否具备足够的认知功能,特别是针对参与试验可能导致的伦理风险,如病理标志物高危状态等隐私信息外泄等,受试者需对相关利弊进行综合权衡,即充分评估患者同意入组进行早期干预的获益及可能受到的伤害。
1.2 受试者受辱及歧视伦理学问题
参与预防性试验的受试者,或许可从研究获悉到自身疾患易感信息,由此引起伦理学层面的问题。与AD相关的认知障碍,常伴随着受辱及歧视问题,如进展性认知障碍的受试者,困扰其自身社会距离感。
其次,与根据临床症状确诊的AD患者相比,临床前期的受试者因其已标识AD潜在性诊断,但缺乏认知功能及行为症状的确诊,是否会产生类似的受辱及社会距离感?
另外,标识AD风险的患者是否会出现消极情感及行为倾向?对受试者基于各种假设(如根据认知功能下降病况推导严重认知障碍的可能性)而作出患病标识,是否会产生上述相类似的消极影响?
有研究者针对此类问题进行研究,并指出,“ 导致患者倍感受辱的根源,并非AD疾患标签本身,而是某些标识性推导,及基于此对患者未来功能下降或状态恶化的臆测”。这些发现提示,为减少受试者的受辱感,可对疾患加强正确的宣传教育,让患者明晰其处于疾患临床前期,会经历一系列发生、发展的临床阶段症状期,并非必然进展到AD等严重认知障碍。
另外,对于AD高危人群,除倍感受辱、社会关系疏远等问题,也会引发相应就业、各类保险歧视的忧虑。例如,受试者参与先前AD预防性试验出现淀粉样蛋白风险状态,或许会被记录在病历或其他医疗档案中。当前国内尚未构建适用于保护患者免受保险及就业歧视等相关法律条例,以保障疾患易感人群在病情症状显性之前的基本权益,防止雇主及医疗保险机构歧视性差别对待。因此,有必要加强立法保护,同时优化试验研究设计,以减少受试者高危风险信息的外泄。
1.3 受试者隐私风险问题
在缺乏积极有效的防治措施的情况下,受试者AD高危风险信息外泄,除可能会导致受辱及歧视问题外,还会给受试者带来不少情志影响。鉴于痴呆临床试验相对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一旦疾患的风险评估为受试者所获悉,将会产生系列消极效应。如在临床前期阶段,由于病理标志物阳性类信息或许会导致其心理负担或情感受累,研究者需特别关注参与试验的受试者。尽管疾患易感信息披露或许会给研究带来某些效益,可研究者需对其受益/风险进行综合评估,包括受试者是否具备必要的能力为其未来计划,是否可自主抉择参与相关预防性试验,特别是涉及AD高危风险受试者招募的研究。
关于AD风险测评与教育(Risk Evaluation and Education for Alzheimer's Disease,REVEAL)的试验结果表明,可以减缓疾患相应的心理压抑或情绪低沉效应。该试验指出,“与那些仅获知年龄、家族史、性别相关风险信息的患者相比,获悉自身基因型特异性风险的受试者,并没有表现出异常焦虑、抑郁或其他与试验相关的痛楚”。然而,该试验在获得与基因风险相关的载脂蛋白APOE基因型检测结果之前,已经在临床进行标准心理问卷筛查,把涉及重度抑郁、焦虑或有倾向阳性指征的受试者排除在外。为此,经初筛合格入组的受试者均接受过预检测相关教育与咨询。针对病理标志物公开披露层面,研究者可参考此类模式,把相关风险信息与受试者妥善互动交流。
其次,在REVEAL试验中,“在试验开展之后,受试者对研究本身的利弊考虑在改变,特别是对自身基因型风险信息外泄的担忧在持续。受试者并不认为相关检测可为预防措施或后续治疗提供有效的参考价值。相反,这过程加剧了受试者在涉及就业歧视方面的忧虑”。另一项针对无 症状AD人群开展的抗淀粉样蛋白治疗预防性试验(Anti-amyloid Treatment in Asymptomatic Alzheimer's Disease,A-4 Study),旨在构建相对标准规范的流程,针对高危风险信息披露以及信息外泄对受试者各类心理结局指标的效应,进行多层维测评。上述针对信息公开披露的经验数据,可为AD临床前期临床试验涉及的相关伦理学问题提供必要参考依据。